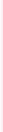|
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
|


慈禧与武则天特有的品质和才能
慈禧与武则天,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,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。首先,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。其次,她们都粗通文墨,像武则天,少年时就阅读了《毛诗》《昭明文选》这些典籍,而慈禧,也是在娘家时,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,会写字,能断句,在那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年代,称得上“知识女性”了,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限。第三,她们都曾垂帘听政,她们身前的傀儡,分别是唐高宗李治,还有清穆宗同治,同治不到20岁便死,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、清德宗光绪。第四,也是更重要的,在她们主政之后,都干出了一些业迹。
武则天一生,果敢坚毅、知人善任、治国兴邦,上承“贞观之治”,下启“开元盛世”,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,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。她称帝后,面对骆宾王的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,声讨她“虺蜴为心,豺狼成性,近狎邪僻,残害忠良,杀姊屠兄,弑君鸩母。人神之所同嫉,天地之所不容”[注1.],她毫无怒色,居然说:“像这样有才能的人,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,实乃宰相之过啊。”[注2.]此等风度,男人未必能有。当然,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,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,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。能成为高权力者,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,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。
谁也没有想到,懿贵妃那个以貌得宠、让肃顺这样的权臣从来不屑于正眼相看的妇人,在咸丰死后竟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。在辅佐儿子同治登上皇位之后,她重用了在咸丰时代靠边站的恭亲王奕訢。[注3.]
道光本来就曾经把六子奕訢当作自己的继承人,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,把帝位传给了奕詝(咸丰),此时,在慈禧的声援下,27岁的奕訢终于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,“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,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。”[注4.]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远见卓识,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,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,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,仅这一项举措,在那个年代,就算得上石破天惊。更何况这些重臣,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,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,开始了学外语(办同文馆)、办外交(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)、开工厂、造机器、修铁路、建海军,大清的面貌,从此被刷新。
当然这需要郑州婚介胆魄。以开办同文馆为例,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相当于外交部)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,自兴办伊始,就受到如潮的攻击。因为这所学校,聘请的多为洋人作老师,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﹐实际操纵馆务,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,不仅学习英、法、俄等外国语言文字,而且在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,增设天文、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。那是真正地“睁眼看世界”,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。两次鸦片战争,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。敢于向敌人学习,奕訢等人的远见卓识,即使今人也未必比得上。试想,在当下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之下,还有谁胆敢声言向日本学习?同治二年二月初十(公元1863年3月28日),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上疏道:
中国与洋人交接,必先通其志,达其意,周知其虚实诚伪,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。互市二十年来,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,其尤者能读我经史,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,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。……我中华智巧聪明,岂出西从之下。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,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,当可由渐通晓,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。[注5.]